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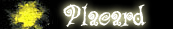
未有公告 

 |
首页 | 相册
55555555呜呜呜。。 我一直喜欢狗不喜欢猫。原来猫猫也是能这么可爱的。。2009-5-26 15:44:10 by 尖叫的陶器 当**总爱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,当年我怎么做呢么辛苦把你养大。。。。 现在的我也是一样,回想月月的时候,就说当年我多么辛苦把你养大,你这不听话的孩子偏偏早早就走了。 所以,月月的可爱倒是写的很少。所幸这些都会一直完整留在记忆里。 猫猫狗狗我都喜欢,各有各的可爱。不过家太小,养了猫咪,再有小狗怕他们不爽。所以,计划推迟到有个大院子的时候 2009-5-26 16:01:35 by 紫晴 当我家里有只狗的时候,我一女同学半夜来敲门,送来了一只10多cm长的小白猫,一只蓝眼睛,一只棕眼睛。好瘦好瘦,拿在手上都提心吊胆的。。(但是弹性很好,直接就上窗台了)。可是,我一觉醒来,我的床单,枕套上全是她的baba。。。5555(夏天,我睡在地上)。。我实在。。。没能力,呼唤了另一个同学给领走了。。。2009-5-26 16:32:30 by 尖叫的陶器 ^_^,那跟月月和帽子差不多。典型的小流浪猫。有一部分从小没有妈**流浪猫不会用猫砂,一定要有大猫教。再说,貌似你那时候也没有准备猫砂。 鸳鸯眼的猫咪很漂亮。我捡过一只叫“粽子”的小猫,也是白毛鸳鸯眼。2009-5-26 21:44:00 by maggiekeen 曾经也养过一只猫咪 也是野猫生的宝宝 刚来我家的时候 连奶都不会喝 我家一点一点把它喂大 他会撒娇 他也是胆小 妈妈天天带他出去放风 然后有一天受到别人惊吓 再也没有回来 等我们找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因为吃了吃了耗子药的耗子走了 他的头都撞平了 因为以前他每回回家都是用头来撞门 不知道他为了回家撞了多少门 2009-5-26 21:48:45 by maggiekeen 看到月月的故事 想起了这只猫咪 真的很难过 所以以后我再不敢养宠物了2009-5-26 22:14:11 by pupu 看得我好心酸好心疼啊 在猫猫狗狗心里头,主人就是全部啊 那个撒娇邀宠的小东西,曾经的心尖尖~~我真的不敢想假如有天秋秋不在了~~~~~2009-5-27 9:08:55 by lily0634 陶器的孩子们都好可爱。不过,我不喜欢养动物,因为有一天他们会不在了,那样的悲伤太令人难过。再加上,肚子里的宝宝才是我的最爱。猫猫和狗狗身上最多弓形虫了。2009-5-27 9:11:44 by 曾家老大 我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,猫狗跟我混只会受罪。2009-5-27 10:50:12 by 尖叫的陶器 maggiekeen别难过,你的猫咪一定跟月月一样回月亮上面了。 失去只会让我们以后更懂珍惜。2009-5-27 16:15:00 by 我是肥手 平实的文字真挚的情感,一点不比那些发表的东东差的,MM好文采。。。别难过,月月是去另外一个环境里玩了2009-11-20 19:56:29 by 豆豆爸爸 唉.养过宠物的,多少都有这样的经历. 陶器好文笔 |
|||||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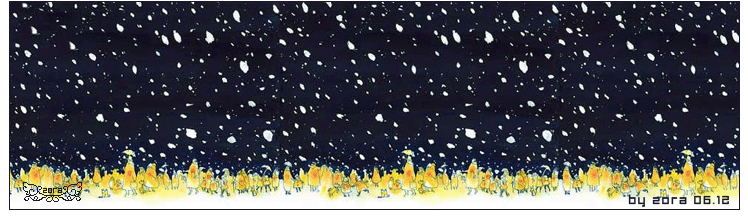

 月月
月月